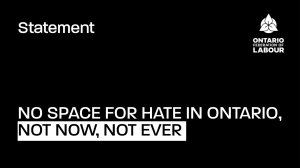現在就是行動的時候–Babbington訪談

PHOTOGRAPH: NADINE MACKINNON
1871年4月12日,一群工人誕生了當時被稱為多倫多行業和勞工議會。代表加拿大當時新興經濟體不同行業工人的16個工會,決心在各處工作場所和社區創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這些工會很快被其他職業有組織的工人加入。不到一年,《環球報Globe Newspaper》印刷工人罷工,導致多倫多行業和勞工議會的許多成員被逮捕,並被指控犯有煽動叛亂罪,該組織的韌力受到考驗。
誰會知道這個群體後來會發展成為加拿大最大的勞工議會, 最終改名為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Toronto & York Region Labour Council)?在其150年的歷史中,該議會經歷了許多鬥爭。該議會在勞工運動中運用教育,同時與尋求改善種族關係和制定立法以保障所有人的公民自由的社區組織合作,為打擊種族不容忍展開了鬥爭。最近,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的成員以身作則,打破了有150年歷史的玻璃天花板。他們擁護牙買加加拿大人安德里亞-巴賓頓 (Andria Babbington),成為該議會的第一位黑人女主席。我最近有機會為《Our Times 》雜誌採訪了安德里亞。
馬克-布朗 (MARK BROWN,下稱布朗):2021年6月3日,你被譽為多倫多和約克地區勞工委員會150年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女主席。告訴我們一點關於你自己的事。告訴我們你是誰,以及你成為勞工委員會新主席的歷程。
安德里亞-巴賓頓 (Andria Babbington,下稱巴賓頓):作為有色人種女性,我也面臨我人生中那份挑戰。我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不得不做多份工作來維持生計。我認識同事和家庭,他們會在一份工作輪班結束時離開,而為了把食物放在桌子上,他們只有到第二個工作場所上8個小時的班。我接觸過工人,他們感到不穩定的工作對邊緣化社區的負面影響。隨著這些問題的加劇和不平等的加深,它影響到所有工人,無論其背景如何。
我擔任勞工委員會副主席教曉我,為了做出能夠對所有社區產生積極影響的變革,我們需要在所有工人中增強政治力量和政治意識。我認為,作為一個勞工團體,我們需要動員起來,爭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我們需要接觸工人,無論他們在哪裡,並告訴他們,他們的工作場所組織工會和投票可以改變他們的狀況變得更好。
在我看來,工會工人可以發揮作用,以實現這一領域的變革。勞工議會必須繼續鼓動反對壓制的和危險的法律,就像它以前反對查驗身份證時所做的那樣。我們必須繼續向工人和社區表現出,我們準備好在工作場所之外為他們而戰。作為勞工議會主席,我們將繼續奮鬥為邊緣化社區找到好工作,就像我們的學徒計劃一樣。
作為一個年輕女性,我不斷被告知,我必須比其他人多做200%,才能在這個國家取得成功。收到這些警告之後, 我睜大了眼睛開始我的第一份工作, 但我肯定還沒有準備好迎接我所看到的。在加入酒店業「後堂」,我加入了一個年長的勞動力隊伍,在我的部門,主要是女性、有色人種和加拿大的新移民。 如果你是新來的,這就是你被派往的地方。
我的同事是他們原籍國的醫生、護士、工程師,但無論如何,我們最終都在「後堂」。 我們很難向上移動。最難的部分是工作場所的不尊重和騷擾。經理們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感謝有一份工作。
布朗:在全球Covid-19大流行時期,你接管了加拿大最大的勞工議會。因此,你預期在任期內會面臨那些獨特挑戰與前勞工議會主席面臨的挑戰有何不同?你認為應對這些挑戰的有效策略是什麼?
巴賓頓:由於這一大流行,我們面臨的一些獨特挑戰,包括在這場大流行之後工人的「公正復甦」想法。我們需要從工人的角度確定公正的復甦是什麼樣子的。這一大流行加劇了以前存在的許多工作場所不平等。許多以前無法獲得15元最低工資的工人,突然被公認為對社會至關重要。這些工人不能在家工作,因此,在大流行期間面臨更大的風險。
我們曾讓醫護人員因工作場所接觸病毒而死亡。我們有教育工作者感染COVID-19,並可能把它帶回家給他們的家人。這場大流行使在家工作的想法有了完全不同的啟示,並且我們只能想像受威脅的公共教育的未來。作為一個勞工團體,我們必須努力實現公正和公平的復甦,使工人、他們的家庭和我們生活的社區受益。
布朗:你認為勞工議會面臨的一些最緊迫的挑戰是什麼,作為克服這些挑戰的運動,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巴賓頓: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認為,甚至在COVID之前,勞工就進入了危機狀態。工會化率很低,像零經濟這樣的新興產業崛起,正威脅著我們取得的許多成就。現在,大流行病及其後果只會使情況更加嚴峻、更加緊迫——這個國家的勞動人民處境更加危急。
要使勞工成功,我們需要回過頭來,把精力重新集中到最緊迫的事情上。我觀察到的一件事,在我參加運動的20多年裡,勞工總是有很事情懸而未決的–階級戰爭正在對這個國家的勞動人民在很多戰線上發動,它迫使我們分散去打每一場戰鬥。有時候,我認為我們把自己分散得太細了。
我希望工人勝利
但我想贏,我希望這個國家的勞動人民能取得勝利。為此,我想將工作重點重新放在組織上,並確保成員參與度提高。我們需要到達每一個罷工、糾察線和工業行動的地方,這是我們主要關注點,而且我們要事先做好準備工作,以確保工人做好準備一路走下去。
為了讓這種能量重新投入到勞工運動中,我認為我們需要的主要事情之一是勝利,簡單明瞭。我們需要透過我們的行動,透過他們的實質收益,而不僅僅是文字,向工人展示運動的力量。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如果我們不能贏得這些戰鬥,人們不會想參與,這只會確保我們在未來更多的損失。人們需要準備好戰鬥, 準備真正誓死抗爭到底。但首先,我們需要向他們展示這是值得的。
如果COVID向我們展示了一件事,那就是老闆們沒有虛張聲勢。我們需要向他們表明我們也不是。
布朗:最近在加拿大各地前寄宿學校的房產上發現了沒有標記的墳墓,這迫使加拿大人重新思考一些人所說的加拿大常見的敘述。敘述將加拿大描述為一個寬容和有禮貌的人的多樣化大熔爐, 沒有在美國經歷的可怕的種族緊張局勢。許多人第一次使用諸如「和解」之類的詞語,因為它涉及到原住民社區。與原住民社區的和解對你有什麼感覺,勞工在這一進程中將發揮什麼作用,如果有的話?
巴賓頓: 對於我個人來說,這個被暴露的真相非常令人不安。一段時間以來,工人一直在為原住民伸張正義,但這只能說明政府在使事情變得正確方面做得很少。2015年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 上臺時,有一線希望,也許事情會改變,但他幾乎在每一個任期都辜負了這個國家的原住民。
現在不是另一個查詢的時候
我們現在聽到一些關於小組討論、研究問題、將問題送到大型智囊團來解決的事情,雖然我很高興人們的聲音會被聽到,但事實是:我們知道原住民社區面臨的問題,他們多年來一直在痛苦地抱怨這些問題!
現在不是派出另一個代表團,開始另一個調查的時候,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行動意味著傾聽原住民領導人已經發出的呼籲,如頒布真相與和解報告的所有建議,向每個社區提供清潔飲用水,聯邦政府必須停止將寄宿學校倖存者告上法庭。 就勞工而言,與工會黑人成員聯盟(the Coalition of Black Trade Unionists, CBTU)和亞裔加拿大勞工聯盟(the Asian Canadian Labour Alliance, ACLA)一道,將原住民領導人納入我們的機構,使成為我們DNA的一部分。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們有一個為原住民及其權利的運動歷史,支持他們的行動,但我們總是可以更進一步。
工會需要評估他們擁有的原住民成員,並盡其所能確定年輕的原住民領導人,使他們在工會中擔任能夠聽到他們聲音的職位。我們需要教育我們的其他成員了解原住民成員的鬥爭,繼續採取行動,並開始認真思考我們如何在本國、工作場所、街道和投票站為原住民提供工人的力量。
我們一些最大的工會是政府工會,我們需要開始創造性地利用我們在那裡的影響力來推動發展。 我們不能僅僅將我們的合同視為工作場所的工具——我們也可以在社區中獲得收益。 如果我們所參與的部門能夠對原住民社區產生積極影響,我們就需要在街頭和談判桌上為他們伸張正義。
布朗:你認為工作和工人權利的未來如何,特別是在加拿大?你認為將要改變什麼,我們需要努力改進什麼?
巴賓頓: 如果我們回到 30 年前,想想工作的未來及其對勞工運動的影響,它可能帶來的鬥爭,我們可能會談論一些工廠工作霧化(好的、穩定的工作變成不穩定的零工工作 ),或一些跨越邊界的行業,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 我現在要說的是,無論你在哪個行業,不斷變化的技術都讓工作變得完全不同。
一個讓人想到的大問題是,圍繞教育界別的混合學習展開的鬥爭。這是一個我認為很多人可能無法想像,我們現在會看到受到重大激變威脅的行業。安省保守黨政府正利用COVID的機會削減教育預算,並解僱教師,迫使他們在課堂上和電腦上進行雙倍時間教學。
政府正試圖裁員,這不僅威脅到當今工人的福祉,也威脅著明天工人的就業前景——而我們的學生也會受到影響,因為他們的學習受到裁員的負面影響。
所有行業的公司都在從這一流行病中吸取教訓,而對於工人來說,這意味著全面失業。老闆們熱衷於擠壓那些因大流行而絕望的工人,讓他們努力工作兩倍,而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卻獲得創紀錄的利潤。它也影響了白領的工作。工作的「線上化」意味著離岸外包、工作時間沒規律,以及工作與家庭之間界限的模糊,使老闆可以從工人身上獲得更多收益,而這些老闆則出租辦公室節省成本。
這些變化現在已成為常態,客戶開始期待它。對我來說,要贏得這場向工人展示的爭鬥,工會密度應該是我們關注的主要領域。我們需要提高工會化率,比以前的高點還要高,並要提高社會意識,確保公司為我們工作,而不僅僅是為老闆的利潤而努力。這將是未來五年的一場巨大戰鬥。
布朗:過去工人中的哪些鬥爭和勝利最能激勵你?
巴賓頓:當我需要一點時間來恢復我的力量,並提醒自己為什麼我們戰鬥,我們可以完成什麼,我總是回想2009年酒店工人崛起運動,這是由我自己的工會UNITE HERE組織。對我來說,它代表了勞工運動處於最佳狀態時的一切。
工人,社區,甚至教會,都聚集在一起,使酒店工人脫離貧困線。我們談論的是一群工人, 他們和我一樣, 大多是移民、婦女和有色人種。這些群體通常是我們社會中最邊緣化的群體,但他們不必在運動期間獨自戰鬥。我為此感到非常自豪,有時我不確定自那以後,我是否能在這個地區看到如此強大的協同努力。
這並不是說我們從那時起就沒有與工會、社區或基層開展過偉大的運動,但這些工作更加孤立,更多的人試圖靠自己來做。令人振奮的是,人們並沒有失去為正確的事情而奮鬥的意志,但我的經驗告訴我,我們不能一個人去,當我們想要贏得大勝利時,就像我們在酒店工人崛起運動時所做的那樣,我們都需要走到一起。酒店工人的崛起顯示了我們是多麼強大, 所以這是一個運動, 我將永遠記住。
布朗:工會黑人成員聯盟 (CBTU)、亞裔加拿大勞工聯盟 (ACLA) 等組織與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有著長期的工作關係。 在你的任期內,你如何看待這種關係? 這些組織是否與勞工議會的工作有共同之處,議是否認為有任何合作機會?
巴賓頓:我的主要關注領域之一將是我們工會中的種族主義。這是我的前任約翰-卡特賴特(John Cartwright)在平等方面取得的進步,也是我個人關注的領域,所以我相信CBTU和ACLA在那方面與我合作是有意義的。
我認為這個難題的第一部分就是看看我們自己的家:工人。我們需要團結起來,制定一個計劃,使我們能夠消除工會中的種族主義。不過, 制定這一策略的不僅僅是我們工會內部的人和高層領導。這是一個影響到我們所有人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從CBTU和ACLA以及社區請來領導,共同致力於這項工作。
我希望在這種倡議中擁有一些可識別的面孔,不僅是我們認識和尊重的社區領袖,而且是我們教授的新一代年輕領袖,我們教育他們,然後與他們一起發展運動。
當我聽說工人在工地發現他們的設備上有套索之類的事情時,我感到很噁心。 剛搬到這個國家時,我處理過這種不寬容,但我無法忍受再想像這樣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 我認為這是勞工議會的一個重要問題,我並不傾向於將 CBTU 和 ACLA 視為獨立的團體,而是將其視為議會本身的核心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歸根結底,一個真正的領導者不是尋求共識的人,而是塑造共識的人,」馬丁-路德-金博士說。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的規模之大,帶來了巨大的責任,同時要求其領導人要有力量、韌性和決心。在全球大流行之後倡導公正復甦並非易事,而且安德里亞-巴賓頓和她的團隊也不會掉以輕心。 顯而易見的是,在後 COVID 氣候中克服困難的挑戰,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加拿大最大的勞工議會日常運作的一部分。
Mark Brown是CBTU執行委員會成員、加拿大郵政工人工會 (CUPW) 多倫多分會司庫 訪問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精彩的紀念網站,慶祝其為工人權利和社會正義而奮鬥 150 年。